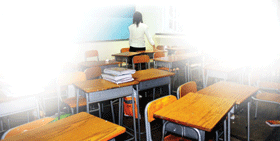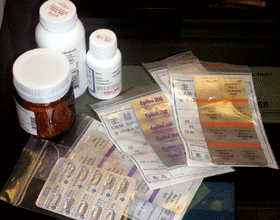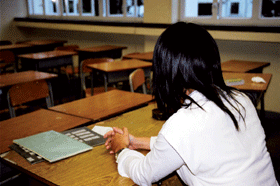抑鬱症蔓延教育界
教師求助無門
記者□駱瑞琪 陸宇光 李以莊 編輯□區穎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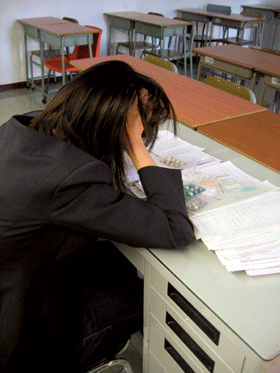
教師是培育下一代的前線人員,理應時刻保持身心狀態良好。然而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情緒中心及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調查顯示,有兩成受訪教師患上不同程度的抑鬱症,估計全港五萬名教師之中,多達二千至二千五百名教師有自殺傾向,情況令人關注。
學生反叛、家長要求高、教育改革帶來排山倒海的工作,加上要維持教師的專業形象,導致部分老師飽受精神病困擾,身心俱疲,萌輕生之念。
29歲的Josephine(化名)兩年前在九龍區一所Band 1中學任教中文和音樂科,因承受不了學生的反叛和工作壓力,曾嘗試燒炭自殺,其後經精神科醫生診斷為抑鬱症。
「我想在學校天台跳下去」
Josephine表示,最大的壓力來源是學生﹕「現在的學生太難管教,不怕你罵,不怕你罰。一有不妥就立即出聲,不會當你是老師。」有一次她為維護一名被排擠的女生和另一名女生吵架,雙方爭持激烈。其後,那女生在ICQ的個人資料欄中辱罵她「無品」、「不夠學生爭辯就哭」,更直言「不會讀好妳教的那科」,這令她大受打擊,以後不敢斥責學生。
家長也給了她很大壓力,有一位家長為兒子申請到外國留學,要求她寫推薦信。家長對推薦信諸多意見,三番四次改動,又批評推薦信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態度惡劣。
零二年五月,科主任指責她教學未盡力,備課不足,指其他新來的教師都很晚才下班,她準時離開便是不對。「我覺得很委屈﹗我已經有很多工作,又是第一年教這所中學,想做得好一點,但沒有時間﹗她以為教音樂科很清閒,音樂科也要備課呀﹗」
她聽到後,當場哭起來,勉強熬過之後的課,回家便燒炭自殺。幸而,她中途放棄了﹕「當時很想死,不過,燒炭很臭、很辛苦。」第二天經社工介紹精神科醫生給她,她被確定患上抑鬱症,告假休息兩個星期。
「整天都想死」
同年九月,她兼讀中文大學教育文憑,有一夜凌晨三時起床做功課。第二天上學時已精神不振,當她友善地和女學生談天時,卻被那學生用惡劣的態度頂撞,令她再有輕生的念頭﹕「當時我回到教員室,在紙條上寫著『我想自殺』,傳給同事,但他竟置之不理,把字條揉作一團扔掉。」對Josephine來說,那一刻受到雙重打擊,她徹底崩潰。「我當時走上學校最高那層,想跳下去一死了事,但當時是小息,有很多學生走動,因此沒有往下跳。」這次她請了一個長假,零三年二月才回校。
「整天都不開心,想死。根本不想上班。」是Josephine患病期間的感覺。經過一年多的煎熬,她終於在零三年五月辭職。壓力令她對教學的熱情盡失﹕「學懂不要太有責任感,即使學生喧鬧,呼喝幾次就算了,無謂把嗓子弄沙了。」她後悔當教師﹕「我不做教師這一行就不會有這個病﹗」
她現時仍在覆診、吃藥,間中仍有尋死的念頭。她覺得社工對她幫助不大,有問題寧願與朋友傾訴﹕「社工的話人人都會說,我不需要了。」她未聽說過教統局和教協對患抑鬱症的老師提供甚麼援助。校方曾為她開過一次會,校長鼓勵同事多關心Josephine,但她認為同事根本不了解她的痛苦。
「我哭了十小時」
現年二十五歲的Joanne(化名),於港島區一所Band 1名校任教普通話及中文科,零二年剛入職便任教會考班。
「我是新老師,不知道怎樣教會考班。學生欠交功課、不帶課本上課,教訓他們又不聽。我對學生和自己都有期望,但學生達不到水平,我很自責,懷疑是否自己做得不好﹖為何不給他們多些測驗﹖
家長的質疑也使她承受不少壓力︰「我的母語是普通話,但竟然有家長質疑我普通話是否流利,又故意問我『普通話』和『國語』有甚麼分別。」
壓力令Joanne出現多種抑鬱症病徵,包括胃氣、不能自制地哭、焦慮、失眠﹕「一星期內有三、四晚睡不著,有時一晚只睡一、兩個小時,從半夜十二時到六時都『眼光光』。我怕自己會做錯事,常擔心做錯了甚麼、忘記了甚麼,又常胡思亂想,怪責自己為甚麼做得這麼差。」長期失眠令她精神不振,曾在講課時腦海突然一片空白。
失控尖叫 喊辭職
零三年十一月初,她的抑鬱症終於爆發﹕「當時回到學校,看見一桌子文件,不禁哭起來,從早上八時哭到晚上六時,無休止地哭,回到家裏,還是一直在哭,哭到看醫生為止。」期間她甚至在電話中對著母親失控尖叫,說要辭職,回到家中又想自殺。
「當時想過如何自殺,想過吊頸、跳樓、用刀,以肉體痛苦舒緩心理痛楚。我覺得自己沒有用,不如索性死掉算吧﹗」可幸,Joanne最後沒有輕生,期後證實患上抑鬱症,需要接受治療。
經過半年藥物治療,她的情況穩定下來。康復的力量來自朋友和家人,她沒有向外尋求援助,覺得校方及教統局並沒有實質措施幫助患抑鬱症的教師。
「學校的幫助令我康復」
有八年教學經驗的Fanny,在一所離島區小學教中文。零四年四月,她一面教學,一面修讀香港大學的碩士課程。當時她因感冒病了一個月,剛巧收到朋友的死訊。之後,她發現自己難以入睡,沒有胃口,脾氣也開始轉壞。
「我當時的情緒很差,會對著學生發脾氣。」有一次她訓導學生時,不知不覺哭了出來,自己覺得莫名其妙。
她其後被證實患上抑鬱症,校長和副校長特別減省她的工作量﹕「幸得到校長、同事的幫助,讓我克服抑鬱症,我現時的情況已好了很多。」
Fanny認為,令她患上抑鬱症的不是學生和家長,而是教統局的政策﹕「學校要跟上教育改革,老師多了很多的工作,在學制改革及整合問題上要經常開會。老師要兼顧行政工作和學生事務。老實說,我們放在學生身上的時間及工夫的確減少了。」
多方壓力令老師患病
來自學校、家長和教改的壓力,成為引發教師患抑鬱症的主要原因。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組織部副主任韓連山表示,一名小學教師嘗試採用活動教學,上英文課時學生變得較嘈吵,校長不認同她的做法,認為上課要安靜,令該名教師質疑自己不是一個好老師,她開始出現精神病徵狀,包括喪失組織能力。今年七月,她被證實患上嚴重抑鬱症,住院期間還不斷重覆說著「我不是好老師」。
韓連山認為教改令教師處理大量文件,參與課程改革,增加教師患病機會﹕「教改推出後,教師每晚開會至晚上八時,又要負責很多行政工作,如寫大量報告,再加上基準試等種種進修的要求,使教師難以專注於教學之餘,又感到專業不受尊重,導致整個教育界的氣氛很差,老師在這種環境中工作自然容易患病。教師不應該做那麼多無關教學的工作。」
教師孤立無援
對於教師因工作壓力太大,而患上抑鬱症的情況,教統局發言人說,教統局已因應教改的需要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及人手,例如﹕學校發展津貼、圖書館主任、外籍英語教師、課程發展主任、優質教育基金及更靈活的撥款安排,讓學校有更多自主和靈活性,按學校的實際需要,妥善調配人手。
教統局呼籲校長清楚認識教育改革理念,按學校的發展階段和未來的計劃,統整教學活動,訂立優先次序,重整工作流程,減少非必要的會議和行政工作,並減少老師兼教的科目和級別。
在建議「3+3+4」學制改革時,教統局表示會輔以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爭取額外資源減輕舒緩教師的工作量。在教師專業培訓方面,教統局也保證會提供足夠的培訓機會,幫助教師為新高中課程作出準備。
但Fanny表示,教統局有所謂「鬆綁計劃」,例如撥錢給學校聘請文員,但效用不大,她覺得教師的工作量依然沉重。而教統局所訂立的「專業支援」,Joanne則認為那其實是要教師持續進修,教師要在三年內上課達一百五十小時,只會是增加壓力而不是支援。
此外,駐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等都是為輔導學生而設,並非為教師而設。Joanne也說︰「不找社工是因為不想加重他的工作量,而且大家是同事,在同一機構內工作,不方便談及工作上的問題。」
某中學駐校社工黎小姐雖曾接觸過校內一個患抑鬱症的女教師,但她表示輔導老師並非駐校社工的責任,社工輔導的對象是學生和家長。
韓連山批評教統局沒有設立任何輔導教師的機制去協助教師舒緩壓力,只依靠民間團體提供有限度支援﹕「一個主宰香港教育制度的機構竟置老師於困境而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