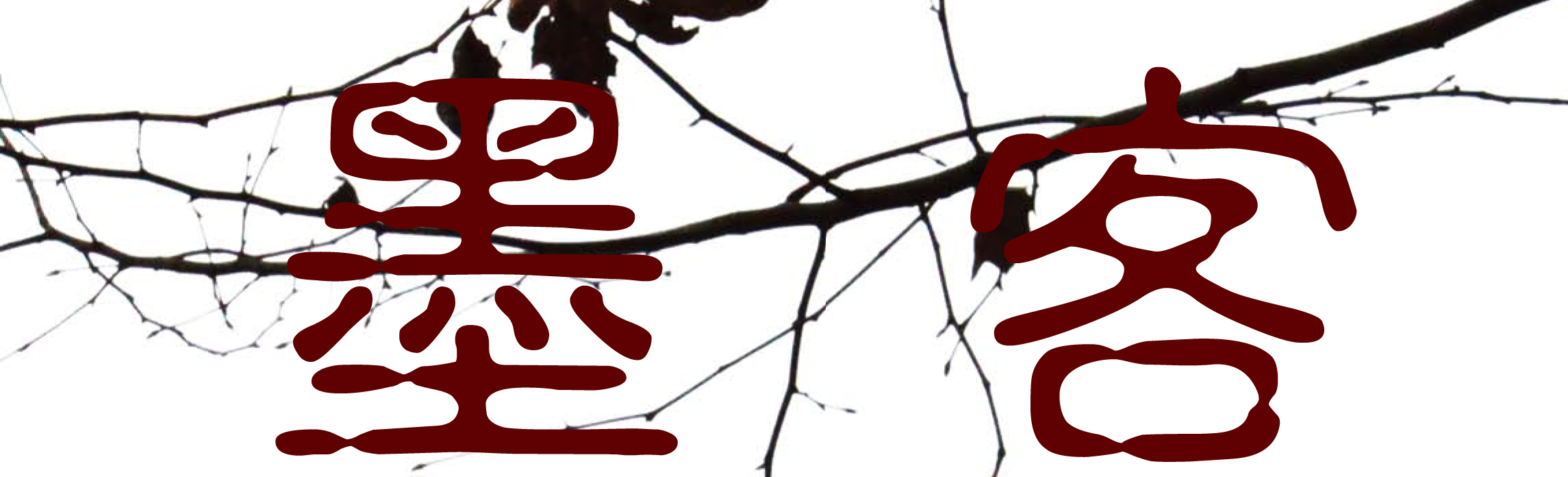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副主任 趙茱莉博士
「墨客」約稿, 自然要找個「騷人」談談;我首選盧梭。手上一本馬君武1918年以文言體譯成的《社會契約論》中譯本,書名翻作「 民約論 」,作者「盧騷 」,確是「騷人」沒錯 。談盧梭,還有遠因。與學生閒聊,談到某個讓同事費解的活動。學生甲說:「 有甚麼不好?娛樂性豐富嘛!」學生乙附和:「讀書壓力大,有人自動給我們調劑,求之不得呀。」學生丙有點不好意思,說:「活動我有份搞……也許真有點無聊……但身為幹事會不跟傳統走,會被人『遺憾 』的。」另一次,有學生來電郵:「對不起,這星期不能來上課,也只好錯過測驗,因為要去某投資銀行的career talk。」啊,一年級生便要為前途操心了?次日再來電郵:「我也想好好享受大學生活,但同班不少同學都去,大氣候如此,我能怎樣?」
如果問盧梭,也許他會搬出《懺悔錄》篇首的話:「我天生就和別人不同。我不比別人好,但至少我和誰都不一樣。」跟別人不同是有代價的,開始時亦未必是自主的抉擇。盧梭在1712年出生於日內瓦共和國,來到世上沒幾天母親就過世了,父親愛在兒子身上找亡妻子的影子,卻又難忘是兒子要了妻子的命。盧梭父親是個鐘錶匠,文化修養卻非一般鐘錶匠可比,父子倆讀遍母親遺下的小說、史書,還有普盧塔克的《希臘羅馬英豪列傳》。盧梭十歲那年遭父親遺棄,往後自有不同的人為他安排要走的路、要信的教,不過每次到了最後,他還是憑自己的直覺和理性決定下一步。
盧梭一生浪遊探險無數,第一次獨自上路還不到十六歲。那時盧梭在日內瓦跟著個刻薄的鏤刻師傅當學徒,覺得自己的品格也墮落了,只能沈迷閱讀。一次在城外散步晚回,城門已關進不了城,索性拋下一切流浪去了。這次流浪讓他遇到華倫夫人,撇開兩人的親密關係不談,盧梭在二十八歲前完成音樂教育、發明自己一套音符系統並贏得獎項,又能博覽群書、燃起當作家的念頭,都始於這次相遇。浪遊讓盧梭接觸不同的人、親近大自然,也是個自我尋索的過程,至死未完。
三十八歲那年,盧梭以《論科學與藝術》一文,贏得第戎學院徵文比賽冠軍。同代的啓蒙思想家都相信,科學是救贖,實證是智慧。盧梭卻認為科學發展與物質文明帶來墮落,學科的興起皆源於墮落;具體說,算術始於貪婪,力學始於野心,物理始於無所事事的好奇,沒有不義便無須法學,沒有戰爭陰謀和暴君便沒有歷史。盧梭獲獎後一夜成名,巴黎的貴族名媛爭著請他出席「沙龍」,其歌劇作品更在路易十五御前演出。這時,盧梭大可接受皇室或貴族贊助專心寫作,但他始終不慣上流社會的造作,終於淡出沙龍,恢復鄉郊獨步。他下半生戀上的不是名媛淑女,而是目不識丁的客棧女僕,或許也反映他在質樸與世故間的選擇。
浪遊冒險,也有極嚴肅的一面。盧梭在《懺悔錄》中嘆道:「一切都離不開政治,有怎樣的政府,就有怎樣的人民。」這種歎喟,實是源於親身的經歷見聞。盧梭漫遊法國,有次路上餓了,就去敲農民的門。農民起初只給他丁點粗糧,後來跟他聊得投契,才捧出紅酒火腿小麥麵包,說:「沒辦法,酒不藏起來就要交附加稅,好麵包讓人見到就要交人頭稅,要是他們知道我還不致於餓死,我肯定就要給搞死。」盧梭在瑞士那沙泰爾湖區遊覽時,路過一小村莊,發覺村內農民都平等相處,沒有頭銜或納稅之煩惱,也沒有職業和技藝的分工,人人多才多藝,靠自己雙手製造所需一切。《社會契約論》提倡公民社會全民自治,不相信代議民主,似是以小城邦日內瓦共和國為典範。不過,書中第五卷提到一群「世上最快樂的農民」,就在橡樹下三五成群共商國事,體現無比智慧,指的更像是那沙泰爾湖的村民。
盧梭四十四歲那年離開巴黎,在鄉郊生活整理書稿,深感自己最偏愛、投放最大心力、牽繫一生聲名的,就是討論政治體制的手稿。六年後,盧梭出版了《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這兩本書一則論政,一則論教育,兩相參照,足證盧梭對文明的態度已從負面批判過渡為積極建樹。盧梭自己未受過正統教育,五個子女出生後都送到孤兒院;五十歲著書談理想教育,想來有其沉重一面。
探尋人類天性,推敲其放棄獨立自主、集結為群的本意,復以「社會契約」闡明政權合法性源於人民授權,盧騷並非第一人。不過,盧梭不同於霍布斯和洛克,完全摒棄君主制度,追求絕對民主。《愛彌兒》強調,人的感性比理性發展得早,所以情感教育應先於理性教育;教育最終目的是培養人的真誠品質,使人自信而不自滿,理智而不冷漠,明鑑善辨但不勢利,自足自立但不自我中心。理想的人該是身心健康、誠實深情、熱心公益。如果全民都接受盧梭提倡的教育,都成為愛彌兒,那麼全民參政、以統一的公意謀求整體福祉也就不是沒可能。
盧梭寫書不用化名,《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出版後馬上遭查禁,盧梭身受其害。打壓他的不只是法國,還有他至愛的祖國日內瓦。盧梭被逼流亡,患上多疑症,可說是為了行使公民權利、篤行公民義務,付出了莫大代價。流放逃逸中,盧梭以自傳體寫成《懺悔錄》和《孤獨漫步者的遐思》,以不加掩飾的感情和意識流風格,重現軼事和風景,紀錄植物和散步,開創了歐洲浪漫文學的傳統。也許,以個人回憶的狂歌來回應政治迫害,亦算是一種精神勝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