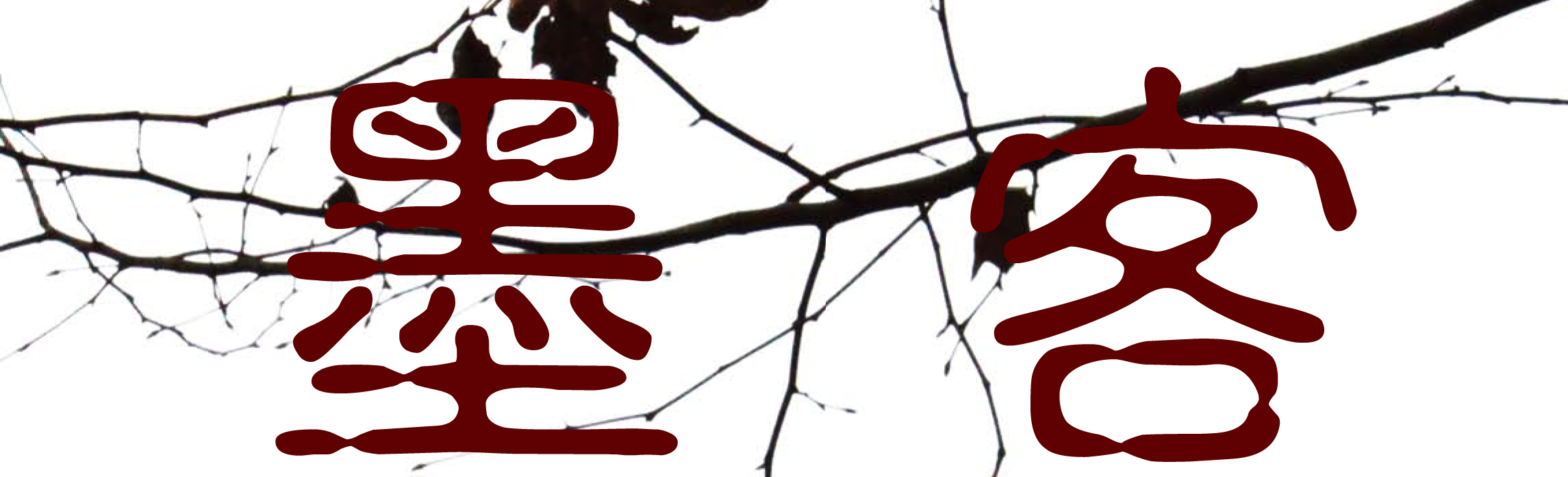
陶國璋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導師
我們活著是為了甚麼?人又是甚麼?這是很普遍卻又難以解答的哲學問題,源於我們心底裡、骨子中滋長出來的焦慮感。我們各人對生命都有所冀盼,但往往又不知其所指為。
這種虛無來自現代社會,源於現今生活:甚麼都太快、太易得到……我們只能在虛無的時空活著,我們甚麼事情也掌握不了,—如飄飄搖搖地站立於虛無的邊沿。
米蘭.昆德拉在其成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Unbearableof Lightness of Being)中點出,現代人並非活在生活的重擔下,而是活在「輕」之中,有種兩腳無法著地的感覺。「……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激烈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愈沉重,我們的生命就愈貼近地面,生命也就愈寫實也愈真實。相反的,完全沒有負擔會讓人的存在變得比空氣還輕,會讓人的存在飛起,遠離地面,遠離人世的存在,變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動作都變得自由自在,卻又無足輕重。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自由的選擇變得毫無意義。」
*
一百多年前,尼采宣稱「上帝已死」,沒有上帝信仰的現代人將步入虛無。這種「虛無的危機」就是人類滿足於現狀而不思考自己曾做過些甚麼,還可以做些甚麼;得過且過,倉促地活著,不斷上網、通電話,這些行為本是極不負責任的,卻被美其名曰為「自由」。
「輕不著地」滲入生活的各個角落。比如,我們不斷透過手機與人對話,大家總是泛泛而談,不斷做自以為是的表達,不斷說「我相信」、「我認為」、「我肯定」之類的判斷;他們爭相議論,不會讓交談停頓,卻無法領會聆聽的可貴。
美國詩人弗羅斯特 (Robert Frost ,1874~1963)的《一條沒有走的路》,寫一個人在樹林中遇上了兩條小路,分別通向不同的地方。這人很想兩條路都試探一下,他對自己說先試探一條人煙稀少的路,回頭再試走另-條。結果是簡單的,他選定了一條之後,還會遇上別的兩條分岔的路、甚至更多的路,再想回頭走當初的另一條路已是不可能的了。當初在兩條小路之間的選擇也許不是很關鍵,但這一選擇的重要性在於,它深刻地影響了這個人以後所要走的道路,這樣,他一生的經歷就會因選擇不同的路而可能完全不同。
*
人生最豐富、最生動的剎那也許就在那猶豫徘徊的片刻,那是生命中懸而未決的時刻。這種猶豫絕不表示優柔寡斷,而是在體味人生的豐富性和多種可能性。那麼,像弗羅斯特和昆德拉這樣的作家之所以與常人不-同,也許就在於他們面臨岔路的時候,比別人佇足的時間更長,他們生活在對可能性的多重想像中。這就是存在本身的一個維度,即可能性的維度。人的生命固然只有一次,但人在各種關頭面臨的選擇,卻可能具有多重的「可能性」。所以昆德拉把存在看成人的可能的場所,從而使「可能性」變成理解人的生存與存在的重要維度。沒有「可能性」這一維度,人就是機械的、別無選擇的,一切都是規定好了的,只有一條路可走。而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和潛在的可能性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