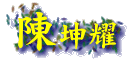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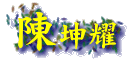
 |
陳坤耀要來個反傳統:於是,他手執著嶺南大學帥印之餘還提起教鞭走進課室;於是,在零零年的畢業禮上他沒有隨俗「唱好」自己品牌的畢業生,卻在廣大傳媒來賓面前批評自己學生的課堂表現;於是,嶺南大學成立了「學風小組」,建議多增校規,以求好好整頓校園的散漫學風。 |
這位唯一執教鞭的大學校長曾享「親民校長」美譽,批評學生質素的大鞭一揮卻害他落得「專制」之名。
其實陳校長都有年輕時。回歸學生時代的陳坤耀,原來早有「造反」細胞,習慣向既有慣例「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反」。
大學時代造反事件
「走堂是天經地義」
陳坤耀於六四年入讀港大經濟系,時值民間抗議風潮的火紅年代。校園之外,陳坤耀不忘到維園靜坐示威,抗議天星小輪加價﹔校園之內,陳坤耀還勇於向一個又一個的權威宣戰。
「我們開宗明義︰lecture is optional, tutorial is compulsory。教授教得不好,走堂是天經地義的。」主修經濟學的陳坤耀顯露出經濟學家本色,屈指盤算成本效益,原來走堂不是懶惰,而是投資策略。「我們會衡量,如果一小時的課堂用十五分鐘自修便可,那麼走堂省下的時間便可多看參考書。」
集體罷食 為表不滿
大學宿舍生活便是讓陳坤耀一展「造反」本領的上佳場地。宿舍生活中,他找到共同挑戰規條的同志友伴﹔訓練出互相配合,以成就大伙兒搗蛋計劃的團隊精神。
| 「那時港大的宿舍規管很嚴,十一時宿舍便會關上大門。」舍監可沒料到大門關了,學生竟轉以木窗作秘道。陳坤耀和同學先虛掩宿舍的某個木窗,玩晚了便從木窗爬進去。每次行事,戰友裏應外合,通報宿舍情況,加上游擊戰術,每次虛掩不同的木窗,敵方難辨虛實,陳坤耀自然手到拿來,成功越過舍監的管治防線。 |
 |
除了暗暗革命,陳坤耀還曾揭竿起義。「我們曾罷食呢!」陳坤耀嘴上泛起勝利笑意。為了表示對宿舍內飯堂膳食的不滿,宿生在飯前協定不到飯堂用膳,結果八十人的飯菜沒有放到嘴裡,卻統統丟進垃圾箱。
搗蛋不忘「分寸」
搗蛋歸搗蛋,陳坤耀對自己大學生身分還是相當自豪的。
六十年代的港大學生總愛把大學襟章掛在衣領當眼處,披上繡有大學標誌的羊毛大衣,在有意無意間「洩露」自己天子門生的身分。巴士來了也不上車,呆呆地與其他乘客繼續等車,只為多讓旁人羡慕。
儘管課外有玩樂的時候,「分寸」二字仍是時刻緊握手中,只要踏進課室,陳坤耀必定循規蹈矩。
「一走進課室,我們便閉嘴聽書,這是對別人的基本尊重。」說到課堂事,陳坤耀收起笑意。
「分寸」是抽象的概念,它不同於尺寸,不能量度。於陳坤耀而言,分寸就是「對人的尊重」。這種分寸,以往的學生從未丟失,可是現在卻失去了影蹤。
一反傳統走進課室
「我愛學生」
繁重的行政工作侵佔大學校長所有時間,往往把他們走進課室的通行證沒收。七所大學中,手執教鞭的校長只有陳坤耀。
他直言:「我愛學生!」。對教學的熱誠令他不甘安坐校長室。他說:「學生給你的回應會令你更喜歡工作。」
學生散漫 感到侮辱
以往陳坤耀只教授三年級學生,學生課堂表現良好。
 |
上學年,陳坤耀轉教一年級學生,這麼一轉非同小可,他發現最叫人擔心的不是學生對學科的理解能力,而是學習態度。
「學生在課堂上自出自入、吃東西、睡覺。這都是當年沒有的,我覺得自己是那麼好的老師,但竟然有學生在課堂上不停談話,令我有挫折感。」 |
學生的表現,對熱中教學的老師來說是種侮辱。他慨歎︰「學生的表現對我是很大的衝擊。」
拋磚引玉 勉勵學生
於是,在去年本應歌功頌德的嶺南畢業典禮上,陳坤耀一反傳統,以自己任教的《經濟學導論》課堂為例,批評時下學生的學習態度,令人感覺矛頭直指嶺南學生。
此話一出,陳坤耀的電郵信箱收到不少同業的支持郵件,曾資助不少教育機構的著名實業家田家炳更主動提出探訪嶺南大學,以示鼓勵。可是「陳坤耀抹黑學生」的批評卻在校園不脛而走。
學生上課態度散漫非嶺南獨有,只是大家心照不宣,把問題藏在課堂內,教室大門一開,依舊拋出大堆讚許學生的說話。家醜不出外傳,陳坤耀破格勇敢「拋磚引玉」,卻令外間把嶺南學生視為劣質學生,令部分學生的自尊受損。 「對學生,我有點過意不去。」面對學生批評,陳坤耀帶點歉意。
增加校規 非罰學生
然而一波未平,「學風小組」的改革建議又翻起軒然大波。針對學生學習風氣的學風小組成立後,建議增加多項校規。校長與學生在遲到十五分鐘、上堂打呵欠等問題上爭論不休,事情愈鬧愈大。陳坤耀慨歎自己的建議被曲解。
「學風怎能憑五條、七條規則便改變呢﹖」陳校長反問。
他強調內容仍在諮詢階段,除了針對學生的規條,還可能配合其他措施。他舉例:「我們也可能訂立《教師上課守則》,教師遲到多於十五分鐘,要重新安排上課時間,甚至遷就學生作個別補堂。」
撥款不足長期抗戰
「嶺南如吊鹽水」
近日風雨,陳坤耀樂觀面對,他認為學生會明白這是善意批評。他也主動向師生發放郵件,解釋始末。可是嶺南的資源問題,卻直教陳校長眉頭打結。
| 嶺南以「博雅教育」為理念,強調小組教學、師生關係和校園生活,讓學生接觸各方面的知識,培訓通才,達到全人教育。可是陳坤耀在任期間卻多次表示政府撥款不足。 |
 |
「如果當局對『博雅教育』的認同一如對科技的認同,嶺南已是世界級學校了。」他形容現在嶺南如在「吊鹽水」。
「現在我們用最少的資金辦最需要經費的教育,很吃力。」他強調這種教育模式需要密集的資源,目前政府以學生人數釐訂撥款數目令嶺南舉步維艱。以零零至零一年度為例,只得二千多學生的嶺南獲得約二億元的撥款,較學生數目約一萬的港大所得的二十三億少得多。
陳坤耀無奈地說:「嶺南現時就如小朋友,未懂行(政府)已不給他糧食,叫他自己找食物。」
寄語學子 放眼世界
春風化雨三十載,從九五年接任嶺南校長,到九九年見證嶺南升格大學,陳坤耀一直面對政府資源不足、嶺南未被廣泛認同等場場硬仗。長期抗戰只因革命尚未成功,陳坤耀仍是戰意高昂,不斷爭取社會及政府對嶺南獨有的博雅教育的認同。對學子,他寄望︰「在校園享受多采多姿的生活,學會分寸,融入社區,放眼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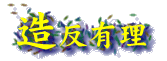
記者 陳巧玲 編輯 黃嘉倩
學生畢業後還會到陳坤耀家中作客。 (陳坤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