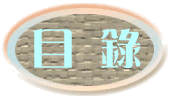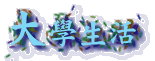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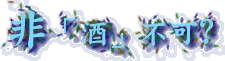
編輯 謝天恩
迎新敬酒 醉中升仙
新生剛升上大學,未正式上課便參與的首個大學活動──迎新營,為大學生提供了豪飲的機會。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麥宏東去年當迎新營輔導員,他說,籌委和大組長飲至酒醉的事件差不多每年都會發生。在迎新營中有「敬酒」的環節,各大組長都會和其他籌委敬酒。「因為籌辦為期數天的迎新營實在辛苦,所以我們會借飲酒來慶祝一番,還刻意灌醉大組長,以求盡興呢﹗」他又補充說﹕「在迎新營中男組長會比較踴躍飲酒,因為要逞英雄,抱著不可以認輸的心態。」
籌備委員和執行委員在迎新營中豪飲,有時學長甚至以喝酒為考驗新生的活動。香港大學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二年級的阿偉憶述,一年前他以新生的身分參加大學某宿舍的迎新營時,上一屆的師兄師姐舉行了一個名為「升仙」的儀式。「他們預備每人一兩支啤酒,要新生把它們喝光。」即使新生可以選擇不喝,但在別人的慫恿下,很少人會拒絕。阿偉指當時有新生參加迎新營後體力不支,喝下啤酒後更因不適而送院。自此之後,那宿舍已禁止學生在迎新活動裏飲酒。
縱使沒有在迎新營沾上喝酒習慣,在往後的組員聚會也可能難逃美酒的魔力。科技大學數學系三年級的蕭錕材坦言是大學活動令他踏上酗酒之路。「入大學前我曾經飲一杯半杯,多數是和家人吃火鍋時才飲,但絕少和朋友飲酒。」
 在迎新營宵夜時,「敬酒」和籌委之間互拼酒量可算是不可缺少的節目。 (中大崇基學二千年迎新營籌委提供) |
然而,在迎新營完了後的小組定期聚會中,師兄師姐們常帶他們往酒吧消遣。漸漸地他們變得豪飲起來,甚至可以用瘋狂來形容。「那時我們『猜枚』輸了就要被罰飲酒,一鋪一罐,一晚十個人可以報銷四十多罐啤酒。後期由於好勝,一晚每人不飲超過十罐都不算『劈酒』。」 |
「莊務」應酬 難免飲酒
除了迎新營外,「莊務」上的應酬活動也常與「酒」有關。「上了大學後,因為上莊的關係,多應酬,飲酒的機會也增加了。」麥宏東直認參加大學活動,令他沾上了喝酒的習慣。
早在中六那年,他已開始嘗試喝酒。不過升上大學之後,麥宏東喝酒的次數更加頻密。「我是中大電台節目的主持,節目完後往往已是凌晨兩三點,於是一大班人就會去吃宵夜,順道去酒吧喝酒,直到第二天早上乘頭班火車回家。」每次到酒吧,他和朋友每人少則喝兩支啤酒,多則喝半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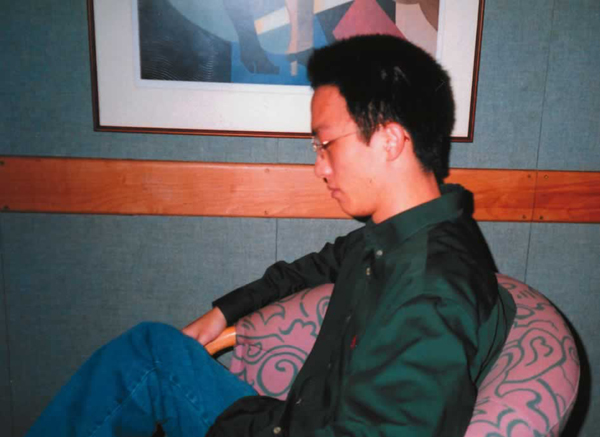 蕭錕材曾受迎新營組員聚會和「莊務」頻繁影響,踏上酗酒之路。 (黎藹霖攝) |
蕭錕材在一年級下學期酗酒,除了是在聚會中受朋輩影響外,也跟「莊務」陷入低潮有關。身兼系會莊員和校報編輯的他因莊務頻繁,煩惱不己。「莊務使我很沮喪,加上當時感情﹑學業皆不如意,才會借酒澆愁。」 |
酒吧聚會多
進了大學,生活模式上的轉變也是部分大學生愛上喝酒的原因。阿偉說﹕「入了大學之後比以前多了飲酒。在大學的社交生活多是和朋友到酒吧聊天,平均兩星期一次,每次都會喝幾杯雞尾酒,久而久之養成飲酒的習慣。」
| 對於大學生喝酒的普遍情況,麥宏東也認為這和生活模式有關。他表示:「中學環境使學生規律性地上學,不容易做一些越軌的事,大學生活時間較彈性。在舉辦活動的過程中除了認識不同類型的人外,還可能沾染了他人的習慣。」 |  麥宏東認為彈性的大學生活使大學生容易養成酗酒習慣。(黎藹霖攝) |
朋輩影響大
其實大學生飲酒的習慣也是受朋輩影響,也有人在上了大學後少了喝酒的。「上大學之前比現在飲得更多,現在反而少了飲酒。」在城市大學唸電腦科學的阿倫(化名)說。阿倫在中七暑假時,因結識了一群愛喝酒的同事而嗜酒。「那時是我飲酒的高峰期,平均一星期飲兩次,每次飲幾罐啤酒。」
不過自從入了大學後,阿倫飲酒的次數由每星期兩次劇減至三個月才一次。「入到大學後心情開朗了。加上可能是我那個系比較乖吧,大學裏的朋友都不太喜歡飲酒。我只會在與中學同學聚會時才會飲酒。」阿倫又認為大學生比較有自制能力,很少會出現大醉的情況。
曾經酗酒的蕭錕材回想酗酒的日子,只覺當時太天真。起初愛上喝酒時,因為酒量好,即使一次喝超過十罐啤酒,也不曾醉過。「最多只試過嘔而已。而我的朋友卻曾經在飲醉後四處破壞路牌﹑亂過馬路,甚至在街上小解呢﹗」
決心戒酒
自從蕭錕材體會到酒對身體的害處後,便立下決心戒酒。「有一次因喝酒弄致胃部不適,要入院治理,出院後便決定從此戒酒,不再糟蹋自己。」蕭錕材自言他已有半年滴酒不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