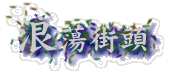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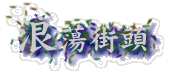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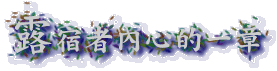
記者 陳智傑/彭佩祺/王珮芝
編輯 廖詠賢/蔡建興
攝影 專題記者/編輯、莊曉陽
時不予我-阿明
身世坎坷 露宿經年
形容枯槁﹑無精打采的阿明,看似一個飽受風霜的中年漢多於一個三十二歲的青年。
|
出身於破碎家庭的他,已斷續過了十多年露宿生活﹕「我兩歲時險遭生父拐賣,獲救後生父出走,生母也於一年後患癌去世,只得與義父和祖母相依為命。後義父因欠債自殺,我便開始居無定所。」 阿明曾因高買和爆竊而入獄兩次。去年他曾在社工協助下租住唐樓,但因無法負擔昂貴的租金,不足一個月便又繼續其流浪生活。 |
 |
他曾在公園長凳和馬場觀眾席上度宿,也曾在街上蹓躂至天亮。尖沙咀金馬倫道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麥當勞是他現在的「家」﹕「快餐店職員不會趕我們走,最多只會把冷氣的溫度調低,逼我們離開。」
努力求職 處處碰釘
阿明一直努力找尋工作,卻常常碰釘﹕「自己只得小六程度,沒有工作經驗,又有案底,加上肺病影響健康,哪會有僱主願意聘用?」
他慨歎露宿者沒有聯絡電話和地址,是求職失敗的關鍵之一。「沒有電話地址『真係好攞命』,僱主因為怕勞工處和入境處來查,不想請沒有聯絡電話﹑地址的人。」現在阿明求職時,會留下社工的電話,或者寫上以前的手提電話號碼。他以前在餐廳工作時很怕遲到,因為如果僱主聯絡不到他,就會「穿煲」,所以精神壓力很大。
「自力更生」計劃嚴苛
所有申請綜援的健全人士都要參加社會福利署的「自力更生求職計劃」,而阿明也不例外。當局要求參加者每兩星期應徵兩份工作,並呈交有關求職資料。所以阿明每月都要到社署報到兩次,讓職員了解其求職進度。「如果兩星期內都沒有找工作,隨時會被停發綜援,遲了報到又會停發租金津貼﹗」
一月份,阿明便因為遲了報到,被社署停發一千五百元的租金津貼,目前僅靠每月一千八百零五元的生活津貼過活。訪問當日他就連吃晚飯的錢也沒有。
面對茫茫前路,阿明只好帶著無限唏噓,再次回到他那燈火通明,但又異常冷清的「家」。
社會福利署高級新聞主任梁婉心強調﹕「自力更生計劃主要是衡量參加者的積極性,即使未能符合兩星期內找兩份工作的要求,就業協調主任仍可行使酌情權,給予寬限。」
救世軍社會服務部特別服務督導主任唐濟方則認為,該計劃並非專為露宿者而設,並不能針對露宿者的困難﹕「自力更生計劃成效不大,因為有些露宿者會在求職時刻意表現欠佳,又或訛稱找不到見工地點。這樣你拿他有甚麼辦法﹖」 以阿明為例,他說自己曾覓得一份送外賣的工作,但想到若長做這份工,社署就會停止發放綜援。在衡量過利害後,他還是辭了這份工作。
拒絕綜援-何伯
跳槽不果 露宿街頭
五十三歲的何伯「住」在旺角火車站附近的行人天橋已兩年,曾經是個月入過萬的麵包師傅。七﹑八年前,他恃著自己有三十年造麵包經驗,毅然辭工,打算另謀高就,卻再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長期失業加上嗜賭馬,很快便花光積蓄,逼不得已成為露宿者。
環顧何伯的「家」,只有一張殘舊的帆布牀和一個裝日常用品的紅白藍袋。日曬雨淋的生活,何伯早已習慣,最難忘的,是九九年一個九號風球的晚上﹕「那時『橫風橫雨』,我只得紙皮蓋身,但最終也渾身濕透,真是饑寒交逼﹗」
|
不找長工 嗜煙如命 何伯一直有倒垃圾﹑拾紙皮以賺取每天幾十至幾百元不等的生活費,抱著「餐搵餐食餐餐清」的心態﹕「找不到工作便吃麵包或飯盒作晚餐﹔賺到錢便到時鐘別墅睡一﹑兩晚,放假充電,花光錢後再回去露宿。」 收入不穩,沒有令何伯作出找長工的打算﹕「散工自由度大,不用受氣,也不會有壓力。」他坦言自己對工作要求很挑剔﹕「有一次聖安娜西餅店以月薪七千元請麵包師傅,但不准員工吸煙,所以我便放棄了。」 |
 |
嗜煙如命的何伯,雖然咳嗽不停,但在採訪過程中仍煙不離手,不消兩小時便抽掉半包香煙。
何伯一直想租房子住,無奈房租太貴難以負擔。問他為何不申請綜援,他說﹕「申請綜援太麻煩了﹗我有手有腳有自尊,不需要政府救濟﹗」他又認為,綜援金額不足以應付日常開支﹕「基本綜援加租金津貼只得三千多元,三餐要七十元,還有買煙和到洗衣店洗衣服,一百元一天也不夠用﹗」 他邊說邊展示自己的牀單被鋪和衣服是何等整潔,彷彿對綜援一點也不稀罕。 「我以前有很多嗜好:看電影﹑跳舞﹑唱K,身邊不愁女伴,戶口曾有八萬元積蓄......」何伯邊說邊向記者展示以前的卡啦OK會員證和舊女朋友的照片,眼裏隱隱透露出對往事的無限唏噓和緬懷。
取消租金按金津貼
社署除向申請綜援人士提供每月一千八百零五元的基本生活津貼,也有提供每月一千五百元的租金津貼。但實報實銷的租金按金津貼已於一九九九年六月起停止發放給身體健全的人士。
對此,梁婉心指身體健全的露宿者應有能力從生活津貼中儲蓄部分作為按金。對於個別有需要的個案,社署仍會行使酌情權給予援助。問到成功行使酌情權的案例,她則表示沒有相關數據可以提供。
|
另一方面,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則反駁,露宿者可由生活津貼省下餘錢作租金﹑按金的講法﹕「每月一千八百多元的生活津貼,平均來說每日只有六十元。既要吃飯,又要買日用品,露宿者還能有餘錢剩嗎﹖」
|
 |
對於有露宿者嫌綜援不足而不申請,救世軍露宿者日間救援中心主任葉秀儀指,不少露宿者將錢全花在吸毒﹑酗酒和嗜賭等不良嗜好上,再多援助也不會足夠。而且不是每個露宿者都積極求職,綜援金額定得太高會令他們過分倚賴。
心理輔導才是上策
唐濟方指不少露宿者缺乏理財概念,連用來交租金的錢也花光。他建議政府在體恤安置之外,為露宿者提供有計劃的心理輔導,解決他們露宿的根本原因﹕「有些露宿者不習慣『上樓』後的生活,覺得十分孤獨,於是又搬回街道上。他們需要的不是金錢或物質上的援助,而是長期有計劃的心理輔導,以適應『上樓』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