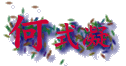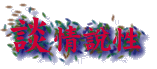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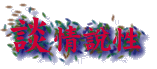
|
|
何式凝,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但更多人直截了當稱呼她為「性博士」。舉凡坊間有一夜情、性濫交等座談會,何式凝往往被邀為座上客,萬眾期待就是她的「性宣言」。 不怕別人亂扣帽子,不怕傳媒「博士賣性」的獵奇眼光,面對記者,何式凝還是落落大方地談情說性,毫不忌諱。 |
開放不是淫賤
「性開放是一個很好的形容詞,是我所推崇的。」
「我不相信這個世界只能有一夫一妻的關係。」所以何式凝選擇同時擁有多個男友的生活。對何式凝而言,「性開放」不過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加一分可能性,添一分寬容:「我只是體現其他生活選擇,給自己開啟多些空間,釋放自己罷了。」
縱然今日女性毋須再揹著「烈女不侍二夫」的貞節牌坊,女方「一腳踏兩船」始終為世所不容,何式凝坐擁三四五六條船,則更有被扣上「淫賤」帽子之虞。難得她對此不以為然,只因對「淫賤」二字另有詮釋。「一般人可能認為『開放』等同淫賤。但『淫賤』不應指性伴侶的數目,而是指對性的態度!」
「對於性,我抱著尋求開心、樂趣的態度,這種『淫』總不會『淫』到『賤』。相反,有些人立心不良,與人發生關係後,卻洋洋得意地四處宣揚,這才是真正的『賤』。」
改變兩性看法
「談性不等於開放,有沒有勇氣談論自己的性問題才是最大的考驗。」
何式凝生長在傳統中國家庭,從小到大一直憧憬「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甜美生活。其後在香港大學完成碩士學位,便順理成章在港大當導師。當時,她覺得自己身為女人,有固定的工作又有感情穩定的男友,已經相當幸福:「我根本沒想過自己需要事業!」
|
然而老天爺似乎另有一番主意。一天,何式凝在教職員室門外看到一個專為初級教職員而設的獎學金。「我只是隨便試探男友的意見,誰知他竟然叫我去申請!那一刻,我覺得應該為將來打算。」於是她便一人上路,負笈英國,完成四年的博士學位課程。 在英四年的留學日子,何式凝認識到天地之大,性觀念也完全改變過來。 |
 |
「以前我以為自己的思想很開放,至少我會做有關同性戀題目的論文,會和同性戀者談論他們的性取向。但是,原來談性不等於開放,有沒有勇氣談論自己的性問題才是最大的考驗。」
外國同學常常帶男友回宿舍,第二天還會討論昨晚的性行為,分享大家的性經驗,這是她從來都不敢做,也沒想過做的事。
回首過去,何式凝慶幸自己沒有嫁作馮婦與男友結婚產子:「這樣反而給我更多思考的空間,改變了對生活的態度。」
「年輕時以為跟男人上床後便要和他結婚;但如果上床後發覺雙方性格不合,難道還要勉強自己去結婚嗎?」
放棄婚姻保障
「五十歲的男人可以找個十八歲的女孩做女朋友,但五十歲的女人還可以找到甚麼呢?」
何式凝自覺十分自我,會將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這份「自重」或多或少是為世所迫:「其實哪個男人不想照顧女人的大小事情,但實際上他是否有能力去照顧你呢?」所以她選擇自己一力把擔子兩肩挑。何式凝笑言女人擇偶甚艱難:「五十歲的男人可以找個十八歲的女孩做女朋友,但五十歲的女人還可以找到甚麼呢?」
生於尋常百姓家,何式凝的兄弟姐妹早已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何媽媽見女兒返家吃飯的男伴如走馬燈,當然擔心這位女兒嫁杏之期。「但她見我無病無痛,生活又開心,而且經濟獨立,毋須家人粗心,她很聰明地選擇不予理會。」但對上一輩而言,婚姻始終是最實惠的生活保障,眼見女兒自動「棄保」,自然一萬個不放心。「她怕我胡胡混混花光錢,擔心我老來無依,所以頻頻催促我儲錢買樓。」何式凝明白家人苦心,所以都樂意就範,乖乖儲錢供樓去。
與學生談論性
「至少我講性,人家不會當我是傻瓜。」
何式凝也常常跟學生談及自己的感情生活方式。她說:「這個世界有太多的可能性,我不希望學生像我們那個年代般,對甚麼事情都一知半解。我盡量讓他們讀書時已聽過、思考過其他的生活模式,不一定只有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才可在社會上存在。歲月悠長,難道在二十歲時便要決定八十歲的日子怎過嗎?」
|
|
以大學教授的身分談性,何式凝不認為有衝突,相反較一般人還要來得方便、優越:「能夠有條件及空間去批評社會是幸運的﹔我有博士學位,又有社會地位,至少我講性,人家不會當我是傻瓜。」若她是同性戀者或愛滋病病患者,她未必有勇氣講性。
|
對於傳媒往往揪住她的性史、性態度作為賣點大造文章,何式凝倒不介懷:「在現今社會,這種多重關係十分普遍,分別只是在於我會公開談論而別人卻絕口不提。我不過讓社會知道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不同的生活態度。」
「當然傳媒能夠表達我所想的,固然是好事,但談何容易呢?」最後還不忘為傳媒說句好話:「傳媒只是寫得不夠好,很少會立心不良刻意描黑的。」■
記者/攝影 梁翠萍 編輯 羅海茵